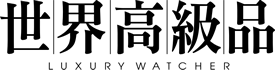文/編輯部
迪奧先生曾在《時尚小辭典》一書中表示:「無論你最喜歡的顏色是什麼,灰色永遠是你可以穿著搭配的顏色。」 Dior女裝暨配件創意總監Maria Grazia Chiuri,在 2020 秋冬高級訂製服系列透過高雅的灰色色調,以一個全新的觀點探索與註解她的秋冬高級訂製服系列,一個集結眾多寓言、熱情,與在這一段似若終止或其時無盡的停擺期間,滋養好奇心所匯聚而成的作品,「我對於這些伴隨神秘及魔法而來的未來不確定性感到著迷」。聚焦於來自三位女性創作者的藝術作品,包含 Lee Miller、 Dora Maar 及 Jacqueline Lamba ,她們早已凌駕於謬思的偶像地位,隱身於她們美麗背後,呈現的是以一個藝術家與超現實主義工作者的眼界,捍衛其女性意識。以超現實主義的影像試圖賦予不可見的事物一種可視的存在,揭示 2020 秋冬高級訂製服系列的設計理念。

Dior 2020 秋冬高級訂製服系列依附一種特殊意念:一個接連、調和自然與蛻變間的系列。其中不乏呈現絢麗的紅色系漸層,宛如珊瑚於海洋繾綣搖曳的光采。 Lenora Carrington 及 Dorothea Tanning 繪製的畫作則於閃爍光影流瀉的夢境中得以延續。
超現實主義下的女性肢體透過全新訂製的微型人台詮釋,以一個更詩意的表現方式來揭示 2020 秋冬高級訂製服系列。藝術家 Cindy Sherman 在她的首部影像作品中便運用了這些奇幻的道具。微型人台反覆出現在時尚歷史和嶄新創作中,現今,藉由這些微型人台實現更多突破固有發表方式的全新儀式。

如同迪奧先生當年的冒險之旅,這些微型的高級訂製服及人台被安放於外型宛若蒙田大道三十號傳奇宅邸的展示箱中巡迴世界各地。遙相呼應當年的「Théâtre de la Mode(時尚劇院)」展覽:二戰後集結法國時裝設計師特別設計的微型作品至歐洲與美國各地巡迴展出,旨在復興法國時尚產業,並為戰爭倖存者募款。 Dior 高級訂製工坊在這趟冒險之旅中擔綱要角。從日間套裝開始,採用男裝面料打造充滿立體結構與建築線條的 Bar Jacket 微型創作,工藝精湛媲美藝術品。大衣呈現褶襉層次、飄逸垂墜剪裁令人聯想到古代神廟裡的神祉雕像;灰色與金色調和的璀璨色澤,使衣裳如霞光閃耀。
這些極致精巧的微型作品全程手工縫製,讚頌高級訂製服不可或缺的美感創意。而於謝幕登場的華麗婚紗,維繫一個隨時間流逝而遺忘的象徵典範。藉由這些微型時裝模特兒,以最自然的方式呈現並重塑高級訂製服裡最引人入勝的線條剪影。

Lee Miller
Lee Miller ,美國模特兒及攝影師,她曾是美國紐約當紅的時裝模特兒,事業如日中天的她卻選擇離開美國與模特兒產業,來到她心中如夢似景的巴黎,夢想成為一名攝影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擔任《Vogue》的戰地記者,報導了諸如倫敦大轟炸、解放巴黎以及布痕瓦爾德與達豪集中營等歷史事件。其中,她還留下了一張舉世聞名的攝影作品:在希特勒自殺的那日,前往他的住所,在他的浴缸中拍攝了裸身像。在當時的保守年代裡,世人認為她叛逆、放蕩,但她依然故我且活得自由自在。

Dora Maar
Leonora Carrington 是一位英國籍的墨西哥藝術家,也是一位超現實主義畫家及小說家。她參與了二十世紀三零年代的超現實主義運動,同時身為二十世紀七零年代墨西哥婦女解放運動團體的創始成員。Leonora Carrington 的畫作表現出女性的性慾,也描繪女性堅定與獨立自主的精神。她的女性形象,大多以巫婆、魔女的形象呈現,畫作風格也蘊含中古時代黑暗隱晦的意象與巫術信仰的特質。
Dorothea Tanning
Dorothea Tanning ,生於美國伊利諾州的蓋爾斯堡。她是超現實主義運動及達達主義的重要參與者。她與二十世紀藝術大師級人物如:馬塞爾·杜尚、薩爾瓦多·達利與巴勃羅·畢卡索等人交好,也成為藝術精英圈的一份子。她是一名女性主義者,從不讓丈夫恩斯特稱她為“妻子”,且終身未育。在她 101 年的生命中,她從未停止過藝術創作,離世後,她留下了數量可觀的創作,作品包含繪畫、雕塑、詩集及小說。

Leonora Carrington
Leonora Carrington 是一位英國籍的墨西哥藝術家,也是一位超現實主義畫家及小說家。她參與了二十世紀三零年代的超現實主義運動,同時身為二十世紀七零年代墨西哥婦女解放運動團體的創始成員。
Cindy Sherman
Cindy Sherman 出生於美國紐澤西,是一位攝影師、行為藝術家與電影導演。她以極具辨識度的藝術肖像聞名。Cindy Sherman 在一系列攝影作品中以自己充當主角,並畫上如各種各異的妝容,並設計如戲劇般的場景及服裝來為照片營造奇幻氛圍,有些時候她刻意女扮男裝,企圖顛覆既有的性別印象。不少女性主義評論家,都認為她是傑出的當代女性藝術代表,她的每一件作品似乎都尖銳的探討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卻又充滿了嘲諷亦或悲哀意念,但她曾說自己並非女性主義者。亦有不少藝術評論家將她列為現代藝術中最重要的女性攝影師之一,並認為她是二十世紀後期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